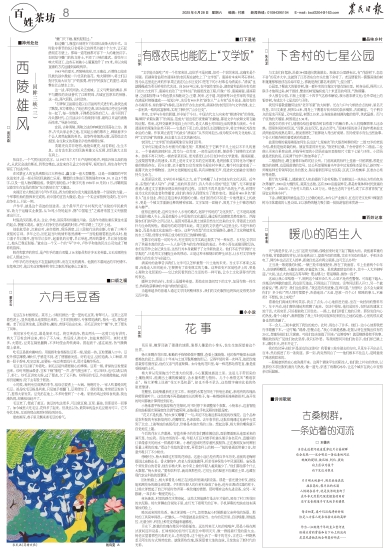“文学能当饭吃?”对一个作家来说,这似乎不是问题,但对一个农民来说,这确实是个问题。而湖南省益阳市清溪村的农民现在就吃上了“文学饭”。清溪村本来叫邓石桥村。因为从这里走出来的作家周立波在《山乡巨变》中把笔下的小村取名为清溪乡,“清溪”也就慢慢成为邓石桥村的代名词。自2018年以来,在中国作家协会、湖南省和益阳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,清溪村启动了“文学村庄”的提质改造工程,印象广场、清溪画廊、清溪荷塘、立波梨园等14个特色景点相继设立;王蒙、阿来、迟子建、刘慈欣等21位作家的书屋也在清溪村相继建成……短短3年,先后有400多名“新农人”“土专家”返乡创业,他们有的办书屋卖书、有的靠写作挣钱,还有的开办生态农场,清溪村的农民因为与文学结缘,走上一条别具一格的致富新路,实现了新时代“山乡巨变”。
其实,文学与乡村的联姻,并非始于今日。中国古代文人向来有“耕读传家”的传统,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”的闲适,范成大“昼出耘田夜绩麻”的勤勉,都是文学与农耕文明交融的证据。然而,这种交融更多是自上而下的,是文人雅士对田园生活的想象与美化。今日清溪村的现象则全然不同——它是自下而上的,是农民主动拥抱文学,将文字转化为改变命运的力量。作家周立波笔下的故乡“清溪乡”从书页间走出,成为现实中的文化地标,这种“文学反哺”的现象,标志着大众文艺的新风向。
农民吃上“文学饭”的清溪现象引发我们思考。
文学何以能成为乡村振兴的催化剂?其奥秘在于它赋予平凡土地以不平凡的意义。一个普通的湖南村庄,因为与一位作家、一部作品的关联,便获得了独特的文化资本。游客不再只为吃一顿农家菜而来,更为感受《山乡巨变》中的文学意境。清溪画廊、立波梨园等景点的建设,本质上是对文学文本的空间再现,是将抽象文字转化为可触可感的物质存在。而当王蒙、迟子建等21位作家的书屋在村中林立,整个村庄就变成了一座露天的文学博物馆。这种文化赋能的过程,具有润物细无声、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持久生命力。
从更深层次看,文学的乡村振兴之力,在于它唤醒了人们对地方的文化认同。近年来,东莞的“素人写作”、沂蒙二姐的田垄诗行、诗人外卖小哥的“低空飞翔”,无不彰显着普通人通过文字重新发现自我价值的过程。当农民不再只是农产品的生产者,而同时成为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,他们的身份认同便发生了微妙变化。清溪村400多名“新农人”返乡创业,背后正是这种认同感的力量。他们回归的不仅是一片地理意义上的故乡,更是一个被文学重新诠释的精神家园。文字如同一面镜子,照见了乡土中被忽视的美与尊严。
值得注意的是,这种文学介入乡村的模式,迥异于传统的“文化扶贫”。它不是将高雅文化强行植入乡土,而是挖掘乡土中固有的文化基因,通过现代创意使其焕发新生。西海固农妇们的写作之所以动人,是因为那是从黄土地里自然生长出来的文字,带着泥土的质朴与生命的韧性。清溪村的成功同样如此。周立波的文学遗产从这里生长,不是外来的施舍,而是当地文化血脉的一部分。这种“内生型”的文化发展路径,避免了文化移植常见的水土不服,使得文学真正成为村民自己的精神财富。
在数字化席卷一切的今天,村庄里的文学实践还提供了另一种反思。乡村让文学回归了其最本真的状态——人人皆可参与的生存体验的表达。外卖小哥在送餐间隙写诗,农妇在劳作之余记录生活,这些行为本身就赋予了文学新的意义。他们不在乎所谓的“文学规范”,只是用文字捕捉生命的悸动。正是这种未被规训的野生状态,让乡村文学保持着惊人的生命力与创造力。
清溪村的故事告诉我们,文学可以怎样重塑一片土地的未来。当文字不再束之高阁,而是走入田间地头,它便拥有了改变现实的力量。这种改变不仅是经济上的,更是心理和文化层面的——它让农民看到自己生活的另一种可能,让乡土文化获得当代性的表达。
播种文学的诗行,本质上是播种希望。那些在田垄间写下的文字,如同作物一样生长,终将收获精神的丰盈与物质的富足。
当越来越多的普通人通过文学找到精神原乡,我们的文化版图也将因此变得更加多元而丰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