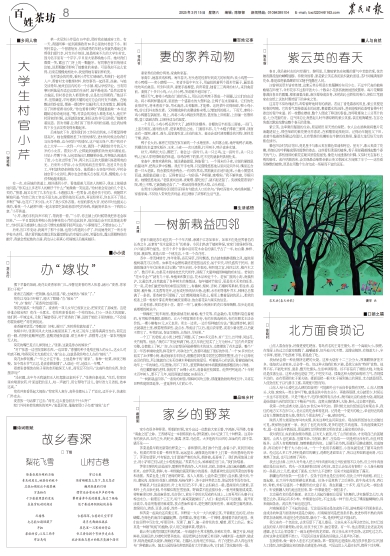山东人喜食面食,好像更爱吃硬面。青岛有名的王哥庄馒头,有一个海碗大小,很硬,在笼屉上热过之后就变暄腾了,越嚼越香,但外地人吃不惯。淄博出锅饼,有锅盖大小,半寸多厚,更硬,干吃很难下咽,都是烩了吃。
我姑姑会烙一种比锅饼还硬的火烧。这种火烧有十二三公分大,厚薄跟锅饼差不多。她每次从老家来,总会带一些。但这种火烧我们吃不着,是我父亲的“特供”食物。他胃不好,不能吃米饭、面条,整天吃馒头,生活单调得很。好不容易有了硬面火烧,对他来说是改善生活。这种火烧也是烩了吃,干吃咬不动。揉做这种火烧的面得有力气,否则揉不动的。还有更硬的杠子面火烧。揉面是把一根木杠子插到墙上的洞里,支点就是面团,人使劲压杠子以代替手工揉,其硬度可想而知。
山东人为什么爱吃这么硬的面食呢?可能跟外出干活自带食物有关吧。山东人把馒头、火烧、窝窝头一类主食叫干粮,就是说其中的水分少。再做得很硬,水分就更少,时间长一点也不容易变质。只是干粮太干,吃的时候得有点汤水,我怀疑北京的卤煮火烧,最初就是给进城干活的农民加工干粮而产生的。卤煮火烧的配料,大肠、肺头,过去都不值钱。
我第一次吃卤煮火烧,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。那时候北京的饭馆远没有现在多,我住的地方又不在市中心,老北京的吃食难得见到。记得是一个夏天的晚上,单位附近的路边有人摆摊卖卤煮火烧,我和几个朋友各吃了一碗,确实好吃。
陕西人管火烧里加肉叫肉夹馍,其实这种吃法河南也有。现在陕西饭馆在北京随处可见,我家附近就有一家。我去了也吃肉夹馍,更多的是吃羊肉泡馍。羊肉泡馍确实好吃,据一位食品学教授说,那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在饮食上最完美的结合。
我对我们山东的面食颇为得意,以为无人能及,吃了山西的面食,才发现自己的孤陋寡闻。山西人也吃面条,但猫耳朵、刀削面、揪片、压饸饹……则是别处没有的,而且种类极多。山西人有粗粮细做、细粮精做的传统。以猫耳朵为例,面揉好后擀成薄饼,切成细条,再切成半个骰子大小的小块,一个一个地用手指碾压,小面块就变成了猫耳朵的形状。经过这么多工序,特别是最后的碾压,劲都吃进面里去了,所以这种面筋道而滑,可以煮熟了加卤,也可以煮熟了再炒。
我去过甘肃,兰州人对外地人把兰州牛肉面叫成兰州拉面很不以为然,但兰州牛肉面确实是拉出来的。我头一次见厨师拉面有点吃惊,面怎么会如此有韧性?小儿拳头粗细的一条面,拉上几把,就成了面条,它为什么不会断?后来才知道里面加了蓬灰。
新疆也有好面条——拉条子。拉条子自然也是拉出来的,但比兰州牛肉面粗,而且上面起棱。比兰州牛肉面更硬也更筋道。拉条子是煮熟了之后再炒,放牛肉或羊肉、西红柿、青柿,炒好后盛到一个椭圆形的大盘子里。我在新疆二十多天,每天必吃一顿拉条子。听说新疆人到内地出差回来,第一件事就是吃一顿拉条子。
北京最有名的是炸酱面。老北京人说起炸酱面总是眉飞色舞的,讲究酱要怎么泻、肉要怎么炒,菜码必有多少种。炸酱面也好吃,不过这是一种干面,吃完了嘴里黏糊糊的,得来碗面条汤。武汉热干面也是这样。
河南焖面是个了不起的创造。无论是汤面还是加卤的干面,滋味都浸不到面条里去,卤或汤的味道与面条的味道是分离的。河南焖面则是把面条抖散,放进炒得半熟的肉和菜里加汤焖熟,味道完全吃进面里,融为了一体,是别种吃法不能比的。
我父亲有一个老战友,去世后留下了孤儿寡母。父亲从来不去拜访老首长,但对已故战友的家人则尽量帮助:给钱、给孩子找工作、抽空看望。有一年,他去看望这位老战友的遗孀,老太太让邻居做了一碗当地特有的龙须面。我父亲从来不吃面条,这回吃过之后,却对这种龙须面赞不绝口。可见民间也有面条的好做法,只是声名不彰。
在我看来,做一碗令人恋恋不忘的面条,第一要紧的还是揉面,现在很多机器可以代替人工揉面,但机器做出来的面条总感觉差点味道。可见这世上凡是好东西,都得下功夫啊。